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动力、安全的基石。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能源发展呈现新趋势、新格局。绿色低碳成为发展主旋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开启新征程,超过一百三十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加快能源低碳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清洁低碳能源发展迎来新机遇,全球能源体系加快转型。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紧密融合,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向低碳化、智能化转变,能源发展模式正在进入非化石能源主导的新阶段,全球能源和工业体系加快演变重构。
能源体系转型,离不开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与能源安全新战略一脉相承,是能源体系不断演进升级从而实现系统性重塑的新形态。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解答了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指明了未来做好能源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
这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趋势新要求,推动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协同互补、融合发展,牢牢把握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本质特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能源支撑。
时代发展、技术进步与能源转型相互促进
从远古开始,人类使用的能源形态就处于不断的转型之中。
回顾能源利用的发展史,人类能源利用史上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能源转型,即从柴薪时代过渡到煤炭时代以及由煤炭时代过渡到石油时代,由此塑造了不同的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甚至塑造了不同的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
从第一次转型说起,英国作为能源转型的代表,其柴薪能源的危机,推动了17世纪第一次能源转型。16、17世纪英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口显著增加,传统手工业如冶炼业、煮盐业、砖瓦烧制、玻璃制造等迅速发展,使得英国原本就紧张的柴薪供应雪上加霜,最终导致森林资源消耗殆尽,引发了“柴薪能源危机”。
柴薪危机,迫使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廉价而丰富的煤炭资源。1550年,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开始超过5%,到1619年,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超过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柴薪。按照能源思想家瓦茨拉夫·斯米尔的量化标准记录,英国完成由柴薪向煤炭系统的能源转型始于1550年,至1619年完成,历时约70年。之后,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长,1938年时达到97.7%的历史峰值。这一转型也代表了由煤炭取代了自有人类以来居主导地位的“柴薪能源”的历史进程。
能源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认为,1700年是人类能源利用的第一个里程碑。因为在这一年的117个夜晚,伦敦城区的路灯会在傍晚6点亮起,午夜熄灭,它所带来的进步,就是进入“从日行性,转变成能够自我控制生物钟”的文明人类。
灯,由“火”而生。由火至电灯,人类走过了长达10万年的漫漫能源转型之路。
第二次能源转型,直接原因不再是能源危机,而是由技术进步推动。其代表是美国。
早在1859年,美国人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打出第一口油井—德雷克井,标志着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但是进入石油工业的发展却经历了两个早期阶段:煤油时期和汽油时期(也称为动力时期)。煤油时期大约从1860年持续到1900年,这一时期石油的主要用途是照明和家庭燃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柴油、汽油等石油炼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得以广泛运用并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主导关键因素。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从勘探、开采、炼制加工到储运和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链。这一时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油田相继被发现。
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二次能源转型从1910年到1950年完成,历时仅约40年。到1950年,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达到38.4%,首次超过35.5%的煤炭比重,成为主导能源。
这次能源转型,石油不再仅限于照明和家庭燃料,而是最重要的内燃机燃料。可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工业革命的推进,一个新的文明—石油文明诞生了。
从以上所述两次能源转型经验来看,能源转型与一个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经济和技术条件。其中,能源资源禀赋对能源转型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比如,以英国为起点的第一次能源转型,在1800年前后,英国煤炭产量就大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产量之和;到184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美国、法国和德国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到18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仍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50%。而这一时期,以美国为起点的第二次能源转型,1880年美国的石油年产量为250万桶,远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在1859—1957年间,美国的石油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能源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和推动力的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1619年,当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超过居主导地位的柴薪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尚未发生。但工业革命开始后,技术进步与能源转型相互促进,便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到19世纪,第一次能源转型向国际社会扩散,德国1815年开始向煤炭能源转型,到1853年转型完成。美国1850年之后开始向煤炭转型,到1885年就很快完成了煤炭的能源转型。
20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二次能源转型逐渐扩散到国际社会。1910年,与美国的能源转型同步,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达到5%。到1965年,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上升至39.4%,首次超过39%的煤炭比重,跃居世界能源消费结构首位,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完成。
能源转型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每一次转型都标志着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与进步。第一次能源转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道,共同推动着世界主要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比如把英国从一个农业小国推到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工业帝国巅峰。
回顾历史,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蒸汽机作为一种新型的能量转换工具,使机械力取代了人力而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动力。虽然生产效率得以极大提高,但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对能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瓦科拉夫·斯米尔所指出的那样,煤炭助力了现代工业的崛起,并在20世纪上半叶推动了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建设。
即使在今天,煤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燃料且在发电行业和冶铁业中持续发挥着突出的贡献。能源结构由煤炭主导转变为由石油主导,这一转变为人类带来了更为巨大的物质财富。石油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能源形式,广泛应用于交通、化工、电力等各个领域,持续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地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能源的使用和驾驭能力不断提升,能源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愈发显现。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能源不仅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美国能源的成功转型,不仅使英、美两国成为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主导力量,而且为两国崛起成为世界霸主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源。
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带动新能源鹊起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愈加紧凑,国际能源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全球能源版图重塑,能源技术革命、新能源产业以及以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生产与供应加速发展,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大幕悄然拉开。
第二次国际能源转型虽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其塑造的国际能源体系是建立在高度依赖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从转型推动力看,虽然技术突破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能源安全的追求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成为第三次能源转型的根本诱因。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新旧能源间的竞争,更是能源消费国的主动选择。
还是从前两次能源转型中的主角英国和美国说起。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煤炭成为主要能源来源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水力、风力和木材等能源被煤炭取代。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使得煤炭能够被高效地利用来产生更强的蒸汽动力,为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
煤炭的燃烧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硫、粉尘、颗粒物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在空气中积聚,形成灰黄色烟雾,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煤炭燃烧还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地球气温逐渐升高。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成为煤炭燃烧带来大气污染的典型案例。由于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物在空气中积聚,导致伦敦市连续多日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造成约1.2万人因空气污染而丧生。
与煤炭相比,虽然石油燃烧产生的污染物种类有所不同,但同样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例如,石油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也是大气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是石油燃烧带来的大气污染的典型案例。由于汽车尾气排放(主要成分为石油燃烧产物)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阳光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导致洛杉矶市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英国成立了能源部,以新的视角审视能源问题。英国通过官方文件的发布、政策的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以及具体计划与战略的实施等措施,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低碳经济并促进能源再次转型。同样,为了应对大气污染,1978年,美国《能源税收法》规定,在汽油中添加10%的乙醇。1979年,美国成立合成燃料集团,致力于煤炭气化和液化以替代石油利用。
1979年,国际能源领域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气候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到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上升,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与石油危机一起推动了新一轮国际能源转型。
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诞生。气候变化由国际会议议题上升为国际公约,形成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此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持续发力,不断推进缔约方履行减排义务。
期间,沙特阿拉伯前石油部长、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创始人之一谢赫·扎基·亚马尼,说出了关于能源转型的至理名言:“石器时代之所以结束,并非因为缺乏石头。同样,石油时代的终结也绝非因为我们的石油枯竭。” 亚马尼的这句话不仅揭示了能源时代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原因,也提醒我们,能源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环境的压力,人类必须积极寻找和开发新的能源形式,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能源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始,人类迈进了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也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进程。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基本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控制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巴黎协定》要求所有缔约方应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并提出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碳中和。
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的深入,世界各国先后将能源转型提上日程,掀起第三次能源转型浪潮。德国率先在2000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03年,英国发布《构建一个低碳社会》的能源白皮书,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在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国的引领下,欧盟成为“全球发展可再生能源最早、力度最大、成就最突出的经济体”。
2007年,欧盟通过了《2020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计划至2020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其总能源消费的20%。2009年,美国颁布《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规定从2012年起,年发电量100万兆瓦时以上的电力供应商须有6%的电力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202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20%,各州在2020年电力供应中的15%以上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2015年,巴西宣布到2030年,该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将升至45%,其中,生物质能源比重将升至18%,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总发电量的23%。
正是得益于清洁和低碳这一根本属性,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在政策引导与技术突破的双重激励下,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重点能源。有数据显示,在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就超过了30%,如果把核能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统计进去,则清洁能源发电已构成了全球发电量的半壁江山。
而在2015—2016年各国新增的发电能力中,可再生能源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化石能源。据统计,2017年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小型水电站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139吉瓦,占到世界新增发电能力的55.3%。如果算上较为传统的大型水电站项目,这两个数字将分别上升至153吉瓦与59.1%。相比之下,火电与核电的新增装机容量仅为54吉瓦与37吉瓦。
从投资量上来看,自2012年起,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领域便获得了远多于化石能源的投资。2016年,各国在可再生能源电站上的投资高达2498亿美元。其中,大型水电站获得了232亿美元投资,占比6%;其他可再生能源获得了2266亿美元投资,占比58%。相比之下,化石能源与核能得到的投资仅分别为1138亿美元与300亿美元。
从国别上看,可再生能源也摆脱了最初仅在发达国家得到重点发展的态势,而在整个世界全面铺开。2004年,发达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达370亿美元,占比64.9%;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投资仅为100亿美元,占比17.5%。随后,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逐渐增大,2015年,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投资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达到了1670亿美元。总体上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球电力供应的重要来源,约20个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了50%。其中,冰岛实现了发电能源的完全可再生化,挪威与巴西高达96%和85%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到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召开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强调人类活动已导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高出1.1℃。这次大会决定,必须加大全球行动力度,并决定要求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2023年12月13日,迪拜气候大会(COP28)完成对《巴黎协定》落实进展的首次全球盘点,达成《阿联酋共识》,核心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努力控制全球升温1.5℃(不发生或有限度的超调),为此,在2019年水平上,2030年实现全球减排43%,2035年减排60%,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二是,以公正、有序、公平方式开启脱离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进程,以便实现2050年全球净零排放。
自《巴黎协定》、特别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以来,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碳中和目标,覆盖全球92%的GDP、89%的人口及88%的碳排放。90%的国家将碳中和目标定在2050年或2050年以后,仅有12个国家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承诺2050年(2007年碳达峰),欧盟承诺2050年,中国承诺2060年前,印度承诺2070年前。
应当看到,以去碳化为标志的全球能源转型时代已经开启。各国既要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推进能源转型,努力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同时要看到,能源转型已成为影响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合作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大国博弈的抓手。
全球能源消费低碳化发展趋势已经出现。气候变化与环境政治的高度结合,代表着全球能源利用低碳化的不可逆转。在低碳化发展大背景下,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增长空间将可能压缩,甚至逐步减少,非化石能源将成倍增长。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自动驾驶汽车、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进步,或将引发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大变革。
能源技术革命加速能源转型向新发展
传统能源是一次性非再生能源。由于不可再生或短期内不可能再生,因此传统能源会造成危机。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两次石油危机确实对每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发生在1973年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减产和提价,导致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上涨了三倍多,对依赖廉价石油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发生在1979年至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封锁,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完全中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石油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了本国经济对石油过度依赖的风险,以及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4年以来,全球能源市场不仅发生了周期性变化,而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的每桶115美元,跌至2015年年底的每桶45美元左右。国际能源市场供过于求、油价下跌,是全球能源市场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共振的结果。石油价格的波动和供应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对国家能源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此,一场能源技术的革新风暴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刻的重塑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版图。在这场变革中,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急剧下滑以及多元化能源格局的并驾齐驱,无疑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
首要驱动力在于,能源技术的革新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成本削减的重要催化剂。随着技术迭代与创新的不懈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效率不断攀升,而成本则呈现出逐日递减的趋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已经大幅跳水,甚至在某些地区,它们的价格已经低于传统的化石能源,这使得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无论是上一轮、还是下一轮能源革命,科学技术都是驱动能源变革的重要因素。就像布鲁斯·波多布尼克(Bruce Podobnik)将能源转型定义为“一种借助技术应用将新的一次能源大量运用于人类消费的过程”那样。科学家通过所发现的自然现象而发明新的能源操控技术、人们进而发明新机器和工具,从而让人类高效而充分使用能源,这是最为关键和基本的一条科技发展路径,会深刻地驱动各方面的科技和社会变化。
正是技术的突破,带来的成本下降,成为当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2010—2016年间,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成本下降了大约65%,燃料发电成本下降67%,光伏发电平均成本降至每千瓦时0.12美元。光伏发电在部分国家甚至可以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与传统能源开展竞争。数据显示,1983—2016年间,陆上风力发电的安装成本从每千瓦4880美元下降至每千瓦1457美元。2010—2016年间,陆上风力发电的燃料发电成本下降了18%,至每千瓦时0.07美元。同期,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的燃料发电成本降低了18%,为每千瓦时0.27美元,海上风力发电的燃料发电成本降至每千瓦时0.15美元。在液体燃料领域,2014年阿根廷、东南亚国家与欧盟的生物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0.56—0.72美元、1—1.3美元与1.05—1.3美元,美国与巴西的燃料乙醇价格分别为每升0.85—1.28美元和0.85—1.28美元,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也已经与成品油价格较为接近,可再生能源相对传统化石能源越来越具有市场竞争力。
能源转型并非简单地将一种能源替代为另一种能源,而是展现出一种多元能源共生共荣的新态势。传统能源在社会的进步中起着基础保障作用,对人类生产生活无可替代。故而在创造物质财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节约能源资源,不断开发新能源、清洁能源,寻找可替代的再生能源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此多元化格局下,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将在一段时间内共存互补。在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既能担当基荷电源的重任,也能作为调峰电源,与化石能源发电相得益彰,共同满足电力需求。此外,随着储能技术的跃升以及电动汽车的普及,可再生能源更是与交通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加速了能源转型的步伐。
从转型的进程上看,新一轮能源转型展现出的不是新的能源形式对已有能源形式的替代,而形成了相互平行的至少两个发展路径。能源技术的革新正在引领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与多元能源的并行发展。这一趋势不仅有助于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因此,我们应积极拥抱这一变革,深化技术创新与合作,携手共促全球能源转型的宏伟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在其著作《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中写道:“我们这些太阳的孩子,可以站在巨大能源成就的浪尖,做好准备,迎接下一次的大跨越,好比纽可曼与瓦特发现蒸汽居然蕴藏着推力与热能的那一刻。”
从理论上说,每年到达地球表面上的太阳辐射能为130万亿吨标准煤当量。全球新能源资源利用时间可达千万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新能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增长的新动力,新能源发展渐入黄金期。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17年世界核能、水电、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总产量达到20.01亿吨油当量,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14.98%,新能源投资总额3335亿美元,接近油气上游投资4080亿美元。随着技术进步,新能源开发利用成本不断下降,与化石能源相比已经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从2024年10月9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可再生能源2024》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太阳能的快速部署,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满足近一半的电力需求。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有望在2030年前激增,2024至2030年期间,新增装机将超过5500吉瓦,几乎是2017年至2023年期间增幅的三倍,大致相当于中国、欧盟、印度和美国目前发电能力之和。从技术看,到2030年,太阳能光伏将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80%。增长主要来自新建大型太阳能发电厂,以及公司和家庭屋顶太阳能安装。尽管面临持续挑战,风能行业将迎来复苏,2024年至2030年装机容量扩张速度将比2017—2023年期间翻一番。在几乎所有国家,风能和光伏发电都是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的最廉价选择。
能源被看作现代生产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从哲学视角来看,其背后蕴含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现代社会中,能源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能源署(IEA)《世界能源展望》指出,过去10年,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82%逐步降至2023年的80%,同期全球能源需求增加了15%,其中40%的增长来自清洁能源。每年有近两万亿美元投资流入清洁能源领域,几乎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领域投资总额的两倍。报告预计,2023年—2030年,在现有政策和市场条件下,清洁能源增量将超出全球电力需求增量的20%。到2030年,全球发电厂的煤炭用量将减少10%,石油消耗量将减少50%。届时,能源系统的碳排放量将首次不再增长。
在碳中和态势下,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已成为各国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共识性举措。
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关系。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但也产生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因此,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势在必行。这种能源转型不仅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钻木取火到柴薪、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再到核能的开发,以至于今天风头正劲的新能源,无一不是能源形态转型的结果,它们都是在变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各种能源形态所蕴含的价值,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能量源泉。
“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本质,就是一部能源发展史。”一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文瑞所说,人类历史上存在三次能源转型,第一次柴薪转煤炭,第二次煤炭转石油天然气,第三次化石能源转新能源。中国已经站到了全球新能源发展的前段,处在C位。如果说,中国引领了“火+柴薪”时代,英国领导了煤炭革命,美国主导了石油革命,中国将可能引领新能源革命。
2329
点击量
2
下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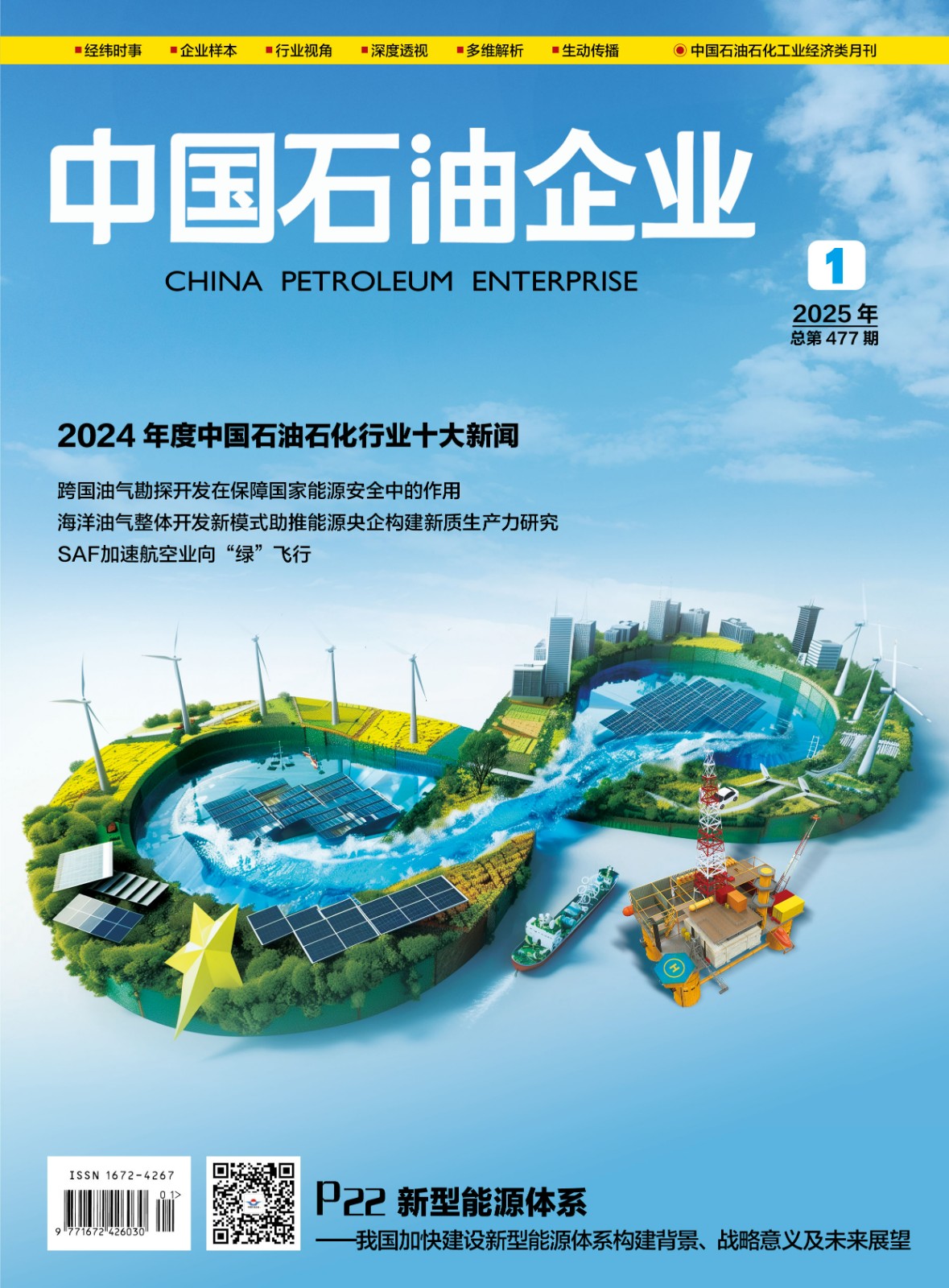
刊出日期:2025.01
主管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企业协会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海洋石油分会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2-4267
国内统一刊号:CN11-5023/F
国外发行代号:M1803
国内邮政编码:100724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0433号(1-1)



